从内卷到躺倒,从充满希望的一代到垮掉的一代,年轻人们总是被冠以不同的标签。在青年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副教授顾文艳看来,她身边的青年正陷入精神搁浅,浪潮退落,一切坚固的东西似乎都在烟消云散。
在她新出版的小说集《一跃而下》中,五个短篇小说里的故事人物几乎都有着现实原型,他们是与顾文艳一同接受了精英教育的中学好友们,在全球自由流动穿梭的“世界青年”,你能看到名校保送、美国藤校、多语背景的duke自我封闭的十年,祝力文穿梭在世界各地的恣意,几乎做到“完美人生”却依旧认为自己一事无成的林书奇......他们或挣扎或从容地延续着自身的优势,而生活的焦虑、阶级的冲突和动荡的世界无一不在审视着他们。
“我与世界的联系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而这个世界早已变得昏暗无常。” 在顾文艳看来,疫情后的焦虑与迷茫是世界青年精神搁浅的缩影,我们如今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世界?未来的出口究竟在哪儿?“一跃而下”则是面对迷茫的自我救赎,他们最终会得到自由,还是虚空?

01 世界青年还在各地穿梭,但精神正在经历危机
界面文化:你在序言中提到,自己已经十年没有写过小说了,写作时创作的躯壳已经锈迹斑斑。那是什么促使你完成了这本故事集的写作?
顾文艳:从时间上来看,写作这件事好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人工湖》和《世界已老》是2022年写的,我想读者或许能够从文字中明显感受到这两篇的剧情和叙事结构并不突出,更多地是情绪的释放,我确实很想用文字记录那段时间,如果当时没有写,现在再想写或许也记不起来了。2023年,我的职业生涯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青椒”压力,在升上副教授后,我开始重新投入写作,也就是这本书中的余下三篇。
界面文化:这本书和你之前的创作有什么区别?你怎么理解这些变化?
顾文艳:我认为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写作风格转向了现实。我过去写的包括《偏执狂》在内的小说是全然基于我的想象,但《一跃而下》里的故事和剧情大部分都有原型。转变的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德国当代文学对我的影响,其中参与性文学(Engagierte Literatur)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也希望自己的写作能更聚焦并参与到社会进程;其次是过去几年的经历,我的职业是看书、教学和学术研究,其实它跟现实的连接还挺少的,这样的感受在前几年更加强烈,当一个人没有办法跟现实产生联系,并且知识和有限的经验都没有任何力量的时候,就会想要一个跟现实的连接口,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思考和反思现实的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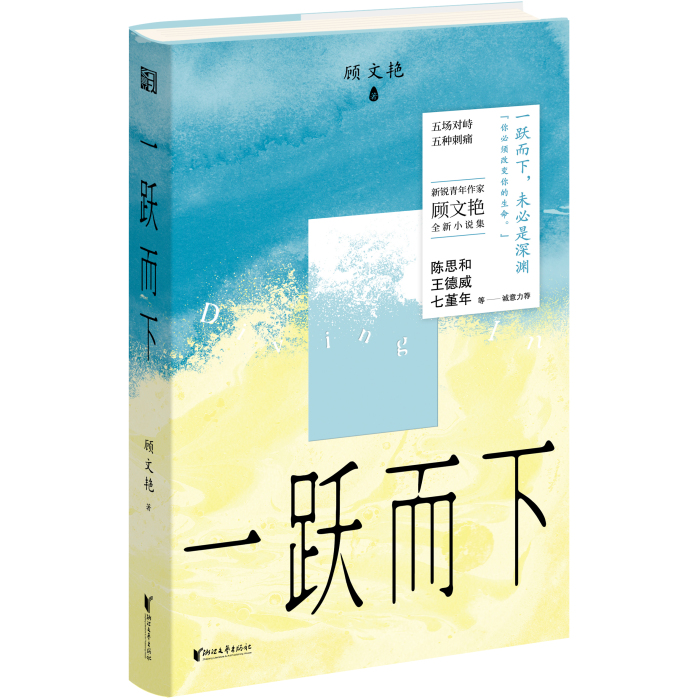
顾文艳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4年
界面文化:你怎么去看待过去这几年的生活?
顾文艳: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代的力量是强大的,当我们对比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时,这种感受就会更加强烈。我刚开始读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时,总觉得那些作品写得很一般,但一旦将其与当代文学对比,你会发现二者背后的差别很大:在一百年前的现代文学里,你能感受到那些或虚构或有着真实原型的人物在被另外一种更强的力量推着走,这个力量可以说是历史的飓风,他们能感觉到,并且会通过作品表现出来。
反观当下,我们90后甚至00后这代人是没有经历过任何风浪的,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像感受不到一丝风的7月。5月我去俄罗斯进行文学交流,有两位作家一位从小生长在深陷战争与冲突的顿巴斯地区,另一位是刚从战争前线回来的空降兵,在他们之后发言的我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但确实就是这样。我在《世界已老》里写过:“有的时候,自由是一种关系,是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这也是我近几年意识到的。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自由是一种可以拥有的东西,二十几岁在国外的时候,我觉得喝酒、抽烟和嬉皮士般的生活可能是自由,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自由其实不是什么能被拥有的东西,而我前几年我才真正发现,你处理任何的问题时候都得跟别人产生联系,跟世界产生联系。
我认为有的时候,我们是想要跟大环境或是大历史产生联系的,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产生联系,甚至没有办法感受到,前几年的生活重新让我感受到了一丝联系,尽管它未必是好的。
界面文化:回到这本书讨论的话题——世界青年的精神搁浅,精神搁浅的背后或许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起作用,你的观察是什么?
顾文艳:这个词应该是编辑老师想的,我觉得起得很好。去年吕晓宇的《水下之人》也办了分享会,活动的主题是“世界青年的狂想曲”,那本书很有意思,作者花了大段时间描写了自己20岁与朋友喝酒的生活,然后突然跳到很多年后大家开始改变世界的生活,确实很狂想,等于说你从一个年轻人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承担起世界的各种事务和责任的人,在那时世界青年这个词就已经被提及了。世界青年这个标签其实与流动有关,我们知道不同阶级有着不一样的流动方式,例如不少研究会讨论晚清的华工流动,但在这里我讨论的世界青年指的是有一定资源、财力和教育经验的,可以一直在世界自由穿梭的那一类人,这些人确实在流动,《仍然活着》中的祝力文就是世界青年的典型,她有能力游历世界,同时她的世界经验也成为了她的部分资本。搁浅的意思就是卡住了,原先流动的世界青年有意或无意地停了下来,无法像过去一样在海上潇洒地流动,同时书里描绘的是精神搁浅,或许这些世界青年的肉身还在各地穿梭,但精神上正在经历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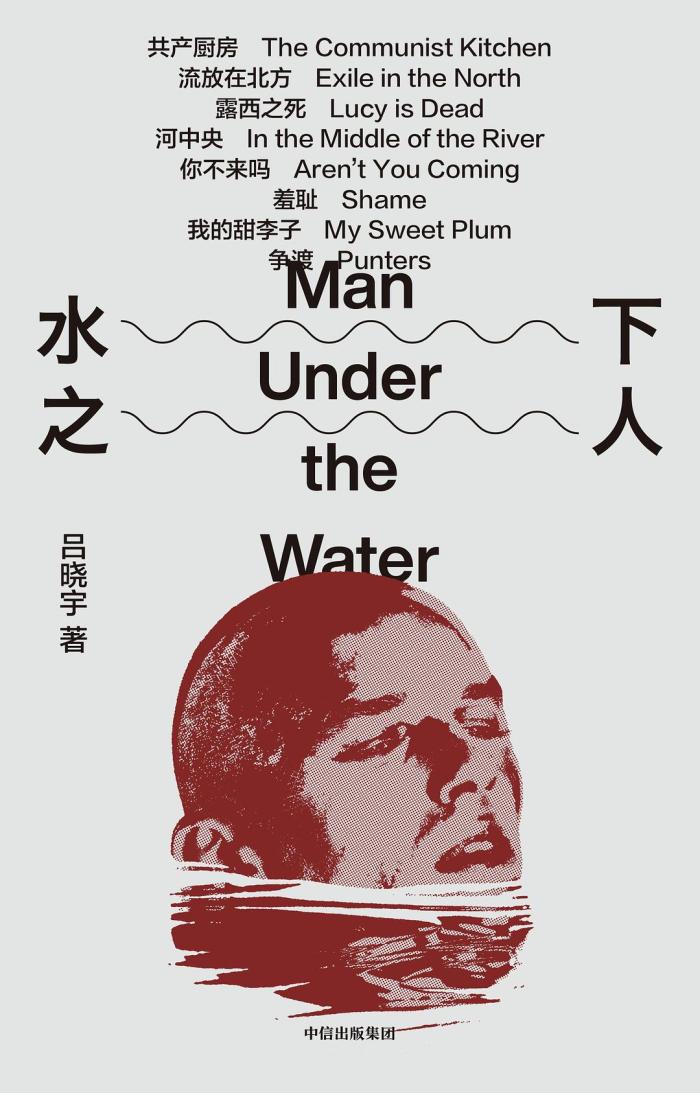
吕晓宇 著
中信出版社 2023年
搁浅是内外部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回看过去十年,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5年我从德国留学回来,经历了难民潮、极右翼和民粹主义运动,我真切地感受到世界开始变化了,紧接着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和不断爆发的局部冲突......尽管一直有冲突,但是你能感受到世界各地的冲突开始加剧了,大历史已经悄然改变,它是导致搁浅的重要外部力量,只不过身处其中的我们感受并不激烈。造成搁浅的内部因素,在我看来是期望难以达成的无力感,举例而言,高中时我们会参加模拟联合国这个活动,大家在其中扮演不同国家的代表,就像是一群人在模拟自己跟世界的联系,然而模联的背后表达的是大家对你的期望:未来的你是必定要跟世界发生关联的,你会有精英才会拥有的,支配性的、统治性的权利,而你必须用精英的力量抵抗住时代与历史风浪。但这样的期望在过去几年当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工作与生活当中存在着许多无能为力的时刻,是那种你会觉得被机制性的东西压着或是被一些制度性内容控制着,个人能动性几乎没有了,甚至有的时候你会想要逃离一份这份体面的工作,这种逃离的心情在很多人那里都有,因为你发现了一些令你不满的东西,你想改变它,但无能为力。
界面文化:无论在序言还是正文中,你都在勾画着自己接受的精英教育的面貌,在《恩托托阿巴巴》这篇中尤为明显。精英教育带给你的是什么?
顾文艳:《恩托托阿巴巴》这篇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活在自我世界中的duke,另一条是身处现实世界的乔良和我。duke的原型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一起在杭州外国语中学读书,他经历了完整的所谓精英教育,但最终将自己封闭了10年,他的故事和感受看起来是那么不真实,但又确实是真的,所以这篇故事我设置了两条线,就好像在两个不同世界中穿梭一样。这个故事中有个有意思的地方,duke长达10年的自我封闭伴随着疫情解封落下了帷幕,即使这两件事情毫不相干,但个人命运与世界进程在这个节点巧妙地重合了。
谈及精英教育,我想先厘清精英的定义。首先,精英必须是被人看见的,如果不被看见或是躲在暗处,那就不是精英,比如运动比赛里就有着精英赛和业余赛的区分,我曾经参加的铁人三项是业余赛,而精英赛就可能会去奥运会。精英赛的存在,就会让人有强烈地夺冠渴望,使其拼命用意志呈现自己的身体,因为会被人看到,被看到就有价值,这个价值不是实际的价值,而是存在的价值,因此外显是精英的核心之一。其次,精英身上是具有支配力量和责任的。我们在中学时遇到成绩好的人会用“他/她很强”来形容,你能在其中感觉到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可以转化为一种支配性的、统治性的,也可以是一种纯粹的或是像知识形式的力量,当你认可精英拥有某种力量时,期待与责任也随之而来,即:当有另一种更强的力量到来时,精英是可以用自己强大的力量抵抗的,在我的这本书里,被标榜为精英的我们显然没有抵抗住。
精英这个词语就像咒语一样围绕在我身边。从中学踏上这条所谓精英的轨迹后,包括老师在内的身边人都会强调精英这一点,就像我在序言中写到的:“我们的老师从我们入学第一天就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我们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我们必须保持最开阔的视野,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然而,离开了校园后,很多同学尤其是看过这本书的序言后,他们都会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在某个时刻,自己所谓的精英人生被卡住了,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停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阻拦着。
02 新的一代必须要一跃而下,跳出原来的世界
界面文化:在讨论过去几年的生活时,你提到无力感,你的序言中也提到,在母亲偏执的努力下,你成为了如今的自己,而你感到疲惫不堪,你如何看待现在大家都感到非常无力的状态?
顾文艳: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跟我的朋友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总会想多完成一点事情,《海怪》中的林书奇超额完成了人生任务仍旧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这不仅仅是代际问题,而是她觉得自己总是“缺了些什么”,我称之为缺陷,她总想再达成某种成就,对自我还有着更高的期待,这又要回到教育的问题,她总觉得自己要做一些对她而言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事情,寻找一种意义感,这样的缺陷很难通过个人努力达成,所以她会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界面文化:怎么理解“缺陷”这个词呢?判断某一方面是否有缺陷的标准是什么呢?
顾文艳:缺陷是消极意义上的你没有拥有的东西,这是一体两面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说成缺陷,但你也可以同时把它说成是没有缺陷,或者说,你可以把缺陷当做可能性,假如你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你有更多其他方面的可能性,所以缺陷指的是你没有的东西。而缺陷存在的意义在于,因为你没有拥有,所以就不用背负着这些上路,因为当你拥有学位学历、职业成就等光环时,你很难抛下这些存在继续前进,但这些包袱太沉重了。
我想在这本书里表达,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抛掉一些东西,并且把缺陷重新找回来,那时候才能感受到更平淡、更深度的满足感,这是我和我的初中同学们讨论出的共识:过去的我们都渴望攀爬和实现更好的自我,在某一个事业里面卷起来,成为一个非常出众的人。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当你要向更高点攀登的时候,你是要舍弃掉一些装备才能接着爬的,或者你突然觉得这条路根本不值得爬的时候,那你就应该跳下去,一跃而下。
界面文化:刚刚你提到,我们想要成就更好的自己,需要舍弃掉一些东西,回归平淡。但现在的年轻一代好像提前步入了这个平淡的状态,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值得我干的事情?
顾文艳: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根据我的观察,我的学生或者更年轻的小朋友们,他们的情绪在两个极点之间跳跃,一会觉得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没什么值得做的事情,一会儿又接着卷进去了。当然,尽管个体间有差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不是不卷的,正是因为激烈的竞争,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到,进而不得不换一条路走或者放弃攀爬。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年轻一代确实有着更多可能性,因为他们很早就发现眼前的道路是有问题的,至少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发现这一点。
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没有觉得一切是那么不值得追求的,或者我的个性本就如此,我一直认为我的原型是浮士德,想要去看到更多的世界,去追求更多的知识,对外界有一种渴望,总觉得不满足。但问题就在于,浮士德要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是要从书斋走向外部世界的,然而我们早就走出去了,但是最终却发现走出去也没有用,或者走出去也不是真正走出去,所以才会有精神搁浅的问题。年轻一代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命题,并且他们很早就发现了。

界面文化:你觉得年轻人的一跃而下带来的更多是希望吗?
顾文艳:我觉得新的这一代人必须得一跃而下,跳出原来的世界,否则他们的生存环境就太逼仄了,机会少、可能性小且意义寥寥。正如我刚才说的,现在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比如一些稳定的工作的缺失,这就意味着需要新一代有更多勇气去做其他事情,或者说开辟新的道路。
界面文化:你在文中写道,2022年夏末的上海浦东前滩是平缓的灰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在其他短篇中,你同样在用灰色作为某种意象,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顾文艳: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提到,“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 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我很喜欢灰色这个意象,因为反复涂抹的灰色不会反射颜色变幻,进而,五光十色世界里难以辨别的真相就这样裸露出来了,我想表达的也大抵如此。无论是对于灰色的前滩的描写,还是对我本真颜色的刻画,2022年我们的世界都仿佛被放置在了黑白之间,一些平时难以觉察的东西被看到了。聚焦到写这本小说的时间,我在过去的几年透过灰色,看到了推动事物发展的一些机制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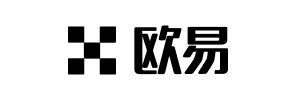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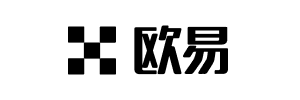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